
人常说,爱国和爱情是文艺作品两大永恒的主题。从人性上讲,古今中外,凡夫圣贤大概是一致的。不必说《梁祝》的柔婉缠绵、《共青团员之歌》的铿锵激昂,也不必说《胡笳十八拍》哀怨缠绵、《义勇军进行曲》的慷慨激昂,只要听《诗经》里所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意即水鸟的鸣叫声都能引发人们对爱情的向往,就可证明音乐的魔力了。纵观历史,对于受奴役压迫的民族,一首独特的音乐便可成为他们一盏不灭的心灯。
雨果说,思想就是力量,而音乐则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心灵魂的独白。听音乐就如一个不吃五谷杂粮的出世之人,站在人生的边缘进行冷静的思考。当我解读《高山流水》重山叠翠、清溪萦回美景,聆听《渔歌唱晚》清虚静泰、恬淡质朴的境界,我便明白,音乐能满足人类情感交流、体验、宣泄、调节等需要。它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使人们找到与人类世代流淌的情态的连接、融合点,能让美好情态流入心灵,使之更纯净、高尚。
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音乐家们的境遇也有惊人的类似:1824年,贝多芬完成《合唱交响乐》时,和失聪抗争多年,创造《命运交响乐》那激情澎湃的旋律时,已经完全失聪,几乎以绝望的呼号作为作品的感情基调;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的一位狂生也把音乐作为生命的绝唱,嵇康生命的最后一刻,弹奏《广陵散》,“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嵇康把内心的极度不平付诸于音乐,而达到置生死于度外,坦然自若的平和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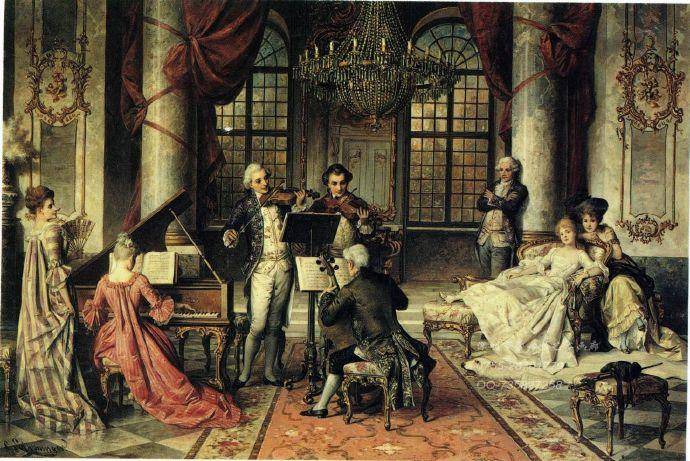
音乐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溪山琴况》中计数琴乐审美之24种况味,即: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亮、洁、润、圆、宏、细、溜、健、轻、重、迟、连……有哲人说过:“音乐的表现是永恒的、无限和理想的。”确是如此,热情、乐观、气势宏伟的音乐可使内敛性格的人摆脱孤寂、羞怯,开阔胸怀,敞开心扉;宁静深沉的音乐可以使外倾性格的人免于浮躁喧嚣,使心境柔和沉静,思索深入细致。
音乐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为何能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带着困惑的心情,我去书中请教先哲。《乐记》说,“乐者,德之华也”;马丁·路德说,“音乐是万德胚胎的源泉”;瓦格纳说,“音乐用理想的纽带把人类结合在一起”;叔本华说,“世界在音乐中得到了完整的再现和表达”;黑格尔说,“音乐的基本任务不在于反映出客观事物,而在于反映出最内在的自我,按照它的最深刻的主体性和观念性的灵魂进行自运动的性质和方式”……

这一切不正是音乐堪当文化瑰宝的铁证吗?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唐朝诗人张祜写过一首《听筝》:“十指纤纤玉笋红,雁行轻遏翠弦中。分明似说长城苦,水咽云寒一夜风。”音乐可以安邦济世,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音乐可使人类的内心世界互相沟通,在共鸣中使个体的心灵与整个人类的心灵交融共振,使一颗颗孤寂的心汇聚在广阔的情感海洋中得到充实和慰藉。
有王维的一首诗为证:“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在中国文人音乐“心超物外”“神游气化”的音韵中,人们会进入“宁静而和谐,空明又无恼,且悠远而千秋长存的自然世界”中去,获得一种超越人与自然的、恒长的生命意识与浩瀚的宇宙精神。
诸葛亮在铮铮的古琴声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刘禹锡调素琴、阅金经;而我没有草庐和陋室,只好在对音乐浓得化不开的爱恋里,抖落身上的风尘,望着前方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