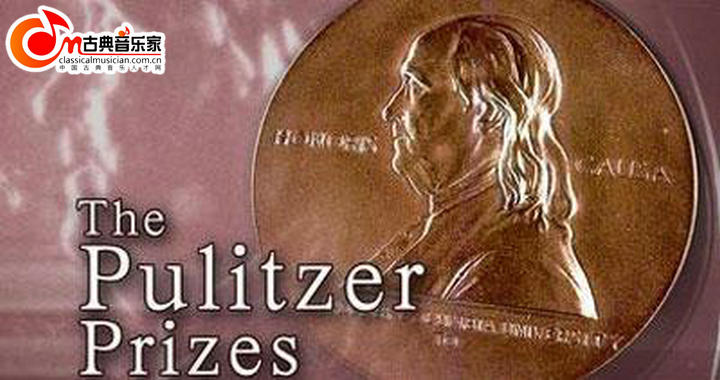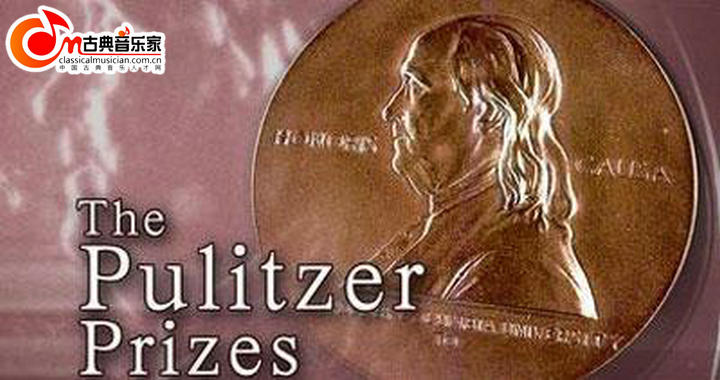
近日,2015普利策音乐奖在美国揭晓。现年57岁的美国女作曲家朱莉娅·沃尔费(Julia Wolfe)以合唱作品《无烟煤田》(Anthracite Field)获普利策音乐奖,并得到1万美元的奖金。该作品于2014年4月26日在费城的一场音乐会中首演,评委会称“这是一出强大的合唱和六重奏清唱剧,唤起人们20世纪初的宾夕法尼亚煤矿生活的关注。”
另外两位获得普利策音乐奖最终提名的作曲家的作品,分别是华裔旅美作曲家梁雷的中音萨克斯风与管弦乐队作品《潇湘》和约翰·左恩(John Zorn)为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创作的室内乐作品《贵族》(The Aristos)。
象征美国新闻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自1943年开始设立音乐奖。美国作曲家威廉·舒曼凭借他的世俗康塔塔《一首自由之歌》成为当年第一位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作曲家。此后,历届获得该奖的人士,均为美国作曲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美国作曲家科普兰、查尔斯·艾夫斯、乔治·格什温、约翰·亚当斯等都曾问鼎普利策音乐奖。
获得普利策音乐奖,对于一个职业作曲家而言,是一件非常崇高的荣誉。2010年以来,一批颇有成就的年轻作曲家纷纷在普利策“榜单”上留名:如2010年获奖的柯蒂斯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美国女作曲家詹妮弗·海格东,因创作歌剧《白蛇传》而获得2011年普利策奖的旅美作曲家周龙以及2012年以“一战”题材为背景的歌剧处女作《寂静之夜》斩获普利策音乐大奖的70后作曲家凯文·普茨。2013年30岁的女作曲家卡洛琳·肖以题为《帕蒂塔》的八声部作品荣摘普利策奖。2014年问鼎普利策的是约翰路德·亚当斯,他试图以乐队作品《成为海洋》唤醒人们对冰山融化和海平面升高的关注。这些获奖者的创作要么关注当下,要么在创作手法上勇于创新。
1943年的普利策音乐奖,来源于遵照当年普利策的遗嘱而设立的每年一度的奖学金,随后才逐渐完善成为大奖制度。普利策对于音乐奖的定义是:“为杰出的音乐创作而设立,该创作必须是当年首演的作品。”2004年,鉴于新作品首演操作的难度,评奖组委会将标准调整“为杰出的音乐创作而设立,该创作必须是当年首演或录音的作品”。
历经了70年的发展,评论界对于普利策音乐奖一成不变的评委班子颇为质疑。2001年,乐评家克雷·甘就认为:“7位评委中全部为男性,而且这个班子始终不变的成员组合本身就说明该奖‘欧洲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性别的局限性。这也从根本上与普利策客观、真实的精神相违背。”2003年普利策音乐奖得主,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也认为:为创作成就进行“划界”的单一标准,会导致作曲家为了迎合“学院派”的口味,而忽视了鼓励多样化音乐创作和思想的危险。
尽管,许多评论家质疑学院中心论的评判标准违背普利策的新闻客观和民主精神,但实际上从历届获奖的作曲家职业背景来看,“学院派”的评判标准仍然是当前普利策评判的主要坐标。历届获奖的作曲家作品,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多样的当代音乐创作手法与传统的经典手法有机结合。
从近几年女性作曲家的创作频繁问鼎普利策也可以看出,这个一向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创作领域,其重心已经开始偏移,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创作领域越发凸显她们的才华和优势。